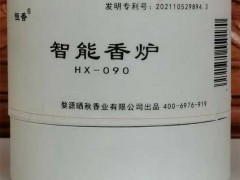香的魂儿,缭绕着,每一缕,散化为非此非彼的独一痕迹,向上,向左,向右,向下。淡了,幻了,无形了。心间的小径,响起轻柔的脚步声。深深地吸气,落定。一块香布,手下抚过。缓慢地,迭起,轻压,任手的掌和指,与棉布的肌肤贴靠。天然素材的纹理,轻唤身体。万物一体。布巾迭好,平铺桌上,"我",准备好定下来。
取小块炭,置于盘中。焊枪抬起,喷出的火射在炭上。火光给炭镶嵌了红红的亮边儿。在强烈的压力下,火,喷泻,急速地旋着舞姿;炭,静静地接纳火的扑抱,一点点红了,暖了。某一瞬,炭以吸收的热情炙烈地回抱,撞击间迸出浓浓的金焰。火拥抱炭,炭拥抱火。火和炭是相通的。
炭吸足了热量,静静地停着。焊枪的火已经熄灭。与炭热舞后,火已经埋入炭的心里。慢慢地,火和炭厮守着,慢摇着,在看不进的深处。看见了,是炭缓缓地热起来。轻轻把炭镊入香炉,炭跻身于"松针和宣纸"燃成的灰里。"任何两种植物都是相通的。"植物燃烧后,还是相通的。炭和灰,是相通的。不知炭在灰的怀抱里,如何地彼此问候低语。只知道轻轻地凑近香炉,一种甜甜的淡香,散出来。
灰,也是香的。哪一种东西,不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香气?古琴流水般的声音,从角落里一丝一弦地波荡,拨动着烟云一样的魂儿。火的魂儿,炭的魂儿,灰的魂儿,香的魂儿,还有,人的魂儿。
炉中放一片云母,取小小一块沉香,于云母之上。炭的热量,透过灰层,抵达云母,均衡地散发,穿透云母的肌理,与沉香会合。纾缓而沉定的热情,烘着,煨着,勾出沉香陈年已久的深情。"树上必须有足够严重的伤,严重到伤口涔出的树脂凝结成似木非木的树瘤,才结得出沉香。"
这好似生命中的伤痛,伤痛中有顽强。顽强得凝重,凝重后开花。
一滴硕大的眼泪,一朵透明的珠花。
闻香。迷迷地,放下世间尘埃的缠绕,回到,桃花源般清新的山林,看见无数来时的径迹,在自己的心田中,如何萦回。与自己重聚,回到一体,放下评判的是非所以,我就是我。阳面,阴面,都是我。我就是一个存在。而树是树,鸟儿是鸟儿,河流是河流。人是人,鬼是鬼。
香气,被听见了,浅浅的涟漪,在心湖荡漾。心,舞动起来,追随着香气飘过的脚步。许多的香儿,许多的心儿,在小小的空间,交会。
独舞,共舞,群舞,又有什么关系?
闻香而舞。
 客服热线:
客服热线: